近十多年來,我投注大量時間進行臺籍日本兵的口述歷史,傾聽百餘位長輩當年的選擇與心境。臺籍日本兵背負著戰爭創傷,許多人終其一生未能痊癒;遺族則須面對失去至親的痛楚如影隨形,很多故事還來不及記錄下來,曾經分享故事的人就已經不在了。除了研究者之外,戰爭影集《聽海湧》也描繪出大時代下臺籍日本兵的處境與角色心理狀態,用戲劇為這些臺灣子弟留下紀錄,讓更多人憶起並理解那個時代。

我曾對臺灣人在日本時代前往「南洋」從軍懷有神秘的想像,他們如何加入軍隊,又如何到達遙遠的國度,都讓我充滿好奇。
進入研究所後,我翻閱有關臺灣戰爭史的書刊,認識到戰時被日方動員從軍的臺灣人,不僅有派往「南洋」的軍夫,另有率先成為正式軍人的陸、海軍特別志願兵,以及後來徵兵制度實施後的應召者,而他們戰時足跡從廣袤的大陸跨越海洋上的蕞爾小島。
臺籍日本兵為何而戰?不能簡化為「被洗腦」或「皇民化」
曾是海軍一員的太叔公和他的海軍戰友,為我打開了口述歷史的大門。跟這些長輩們面對面交流,讓我能循著這樣的途徑去同感他們的經歷和抑鬱。十餘年間,我像著了迷一般,想要知道更多,投注大量時間進行臺籍日本兵的口述歷史。
。圖片提供/李遷嬌女士.jpg)
。圖片提供/盧金水先生.jpg)
透過歷史當事人的表述,傾聽父祖輩當年的選擇與心境,嘗試著貼近歷史情境,就讓我對當時青年為何從軍這件事,由原本單一扁平的認知變得更加多元立體。就像張登標先生提到所以自願參軍,是因為在學校聽到廣播報導戰況,眼看局勢愈加緊張,覺得年輕人必須挺身而出保衛家園;而盧金水先生告訴我,當時社會風氣鼓吹年輕人從軍,即使內心有其他想法也無法表達,可以說是環境逼使他不得不去當兵;至於李遷嬌女士則是因為戰時生活困頓沒有出路,選擇赴陸軍醫院擔任看護助手,從軍成為她的選項。
藉由他們口說,我逐一解答心中的困惑,觀察到這些抉擇背後存在多重因素,包括殖民當局鋪天蓋地的宣傳教化、敵軍逼近家園的迫切威脅、難以逃避的集體壓力及現實的經濟考量等等,都不能簡單地以「洗腦」或「皇民化」來概括論斷。
戰爭創傷如影隨形,終其一生未能痊癒
那個時代的青年在從軍前,多數人或許從未離開過家鄉一步,有些人第一次離家,很可能就是前往即便在今天也難以到達的地方。隨後在各自的戰場上面臨著生死考驗。
依據日本厚生省(今厚生勞働省)於1973年4月14日公布的資料,日軍在戰爭期間動員了包含軍人、軍屬在內的「臺籍日本兵」共計207,183人,其中高達30,304人戰死,可謂犧牲慘重。
戰後,臺籍日本兵背負著戰友的死亡與戰爭創傷(war trauma),許多人終其一生未能痊癒。遺族則須面對失去至親的痛楚,這種傷痛在他們一生中如影隨形。陳冬女士的父親陳世鐘於1945年1月在馬尼拉陣亡,父親的死成為家族內的禁忌話題。渴望父愛的她只能透過靈媒占卜,尋求與逝去父親的連結;而賴新發先生的父親賴文質,當年為改善家中經濟而從軍,卻不幸戰死在菲律賓。思念父親的他不曾放棄打探父親的最終下落,甚至盼望父親有朝一日能如李光輝(Suniuo,音譯史尼育唔,註)一樣生還返鄉,讓他有盡孝道的機會。
這些遺族大多對父親沒有具體的記憶,但父子(女)之間的血脈牽絆,仍在他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缺憾。瞭解父親戰時的蹤跡,拼湊其死亡的訊息,成為人生的重要願望,彷彿這麼做能使他們更接近自己的父親一些,也反映出戰爭對家庭帶來無比深遠的影響。
被永遠遺忘?還是重新憶起?
臺灣人的戰爭經驗具有多元的面向,既包含「中華民國」的經驗,也有「日本殖民地臺灣」的經驗。這種複雜程度在世界各國中少有比擬。如何公正看待這兩者的歷史記憶,並將其融合成共同的國家記憶,至今仍是一個亟待解決的課題。
2014年春天,我到臺南仁德訪問林正興先生。戰時,他曾以臺灣特設勤勞團的身份派赴菲律賓呂宋島,歷經九死一生才回到故鄉,其後一生,難逃戰爭創傷的陰影,時常在夜晚夢魘中哭泣叫嚷,痛苦呻吟。猶記得那天訪談結束後,老先生反覆說著:「今天終於能把這些事情講出來,很痛快。」、「這些可以成為歷史嗎?真的可以嗎?」聽到這些話,讓我感到一陣酸楚。而他在三年後離世。
。圖片拍攝/陳柏棕.jpg)
我私心認為,所有人的記憶都有其存在的價值,也應該受到尊重,沒有人有權否定對方的經歷。唯有彼此真心尊重,進一步互相理解,我們才能真正達到和解與共生。多元價值的存在,正是臺灣社會最珍貴的資產之一。
臺籍日本兵的世代眼看就要結束了,這些人的故事似乎還沒說完,很多故事還來不及記錄下來,曾經分享故事的人就已經不在了。林正興這群人正默默地一個接著一個離去,這些年下來,我們曾認真傾聽過他們的聲音?是否對他們有了更多的了解?還是他們的故事被掩沒在歷史的沉積中,永遠被遺忘?或者有被喚起、被更多人記起的機會?
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聽海湧》,對著更多人說臺籍日本兵的故事
2024年6月底,我受邀到中山堂參加臺北電影節《聽海湧》首映。導演、編劇及團隊的用心,展現在比想像中還要更好的成果之上。我想已不僅是擬真的特效、嚴謹考證的場景與服飾,還有精挑細選的配樂,最讓我驚豔的是,他們細膩地刻劃每位角色的心理狀態,公正描繪出大時代中臺灣人(臺籍日本兵)的處境。
結束放映及映後座談,走出夜晚的中山堂,已不若白天酷熱,而我想起和劇中少年志遠長得神似的比島俘虜收容所監視員林金隆。這位來自臺中的少年被指控於1944年8月11日在菲律賓呂宋甲萬那端(Cabanatuan),「蓄意且不合法」地以步槍射殺美國陸軍中尉Robert Huffcutt。戰爭結束後,由盟軍組成的軍事法庭追究少年「罪責」,他最終被判處絞刑,在1946年7月17日於馬尼拉受刑。
而,是誰下達的命令?誰企圖卸責脫罪?定罪標準是什麼?據聞少年是代誰開槍,卻擔負所有的罪?抑或恪守命令卻違反人道的少年,其實落入了「平庸的邪惡」(The Banality of Evil)? 似乎沒有任何人在意。
林金隆才華洋溢,從軍前為「獅王」繪製廣告招牌,未來可能是前途無量的繪師,卻因為戰爭,由於美國陸軍中尉之死,在南國異鄉結束短暫生命。他在軍事法庭接收審判時,無奈甚或放棄的心情,是否也像志遠一樣?當他被套上絞繩,生命永遠停留在22歲的多年以後,除了研究者消耗自我,如使命般想為像他這樣的臺灣子弟留下什麼之外,現在終於也有人開始要向更多人講述他們的故事。
註:二戰期間,日本徵召眾多臺籍日本兵到南洋參戰,史尼育唔(臺灣阿美族人,日名中村輝夫、漢名為李光輝)與同袍走散,孤身在叢林中離群索居,直到戰爭結束30年後才在印尼被發現,後回到臺灣。
【延伸推薦】
影集|《聽海湧》:阿遠被派往南洋擔任戰俘監視員,卻捲入了一場屠殺,被指控為嫌犯的他,在找尋兇手過程中看清了戰爭的本質。
文章|幕後|《聽海湧》導演孫介珩:異鄉感的關鍵是高聳椰子樹,「聽海」成為一種日常儀式
作者:陳柏棕
責任編輯:陳珊珊
核稿編輯:李羏
出刊日:2024.8.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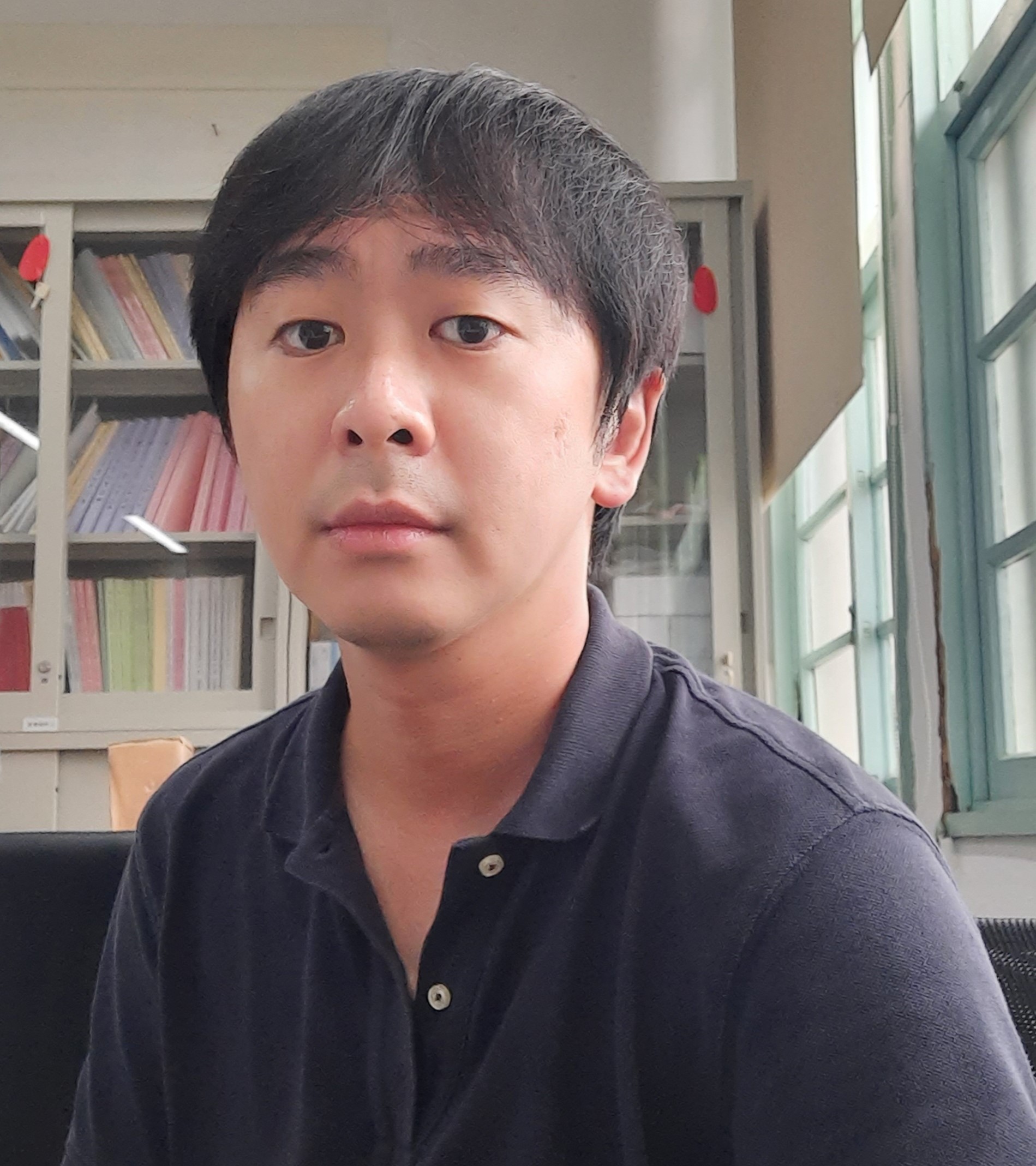
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助理研究員。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畢業,現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著有《軍艦旗下: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1943-1945)》、《護國丸:被遺忘的二戰臺籍海軍史》、《跨越世紀的信號:書信裡的臺灣史(17-20世紀)》與《跨越世紀的信號2:日記裡的臺灣史(17-20世紀)》(共同作者)等論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