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惡的距離Ⅱ》呈現社會應如何以更深層的理解與同理心面對精神疾病與犯罪議題。本文訪談法律扶助基金會執行長周漢威與專職律師唐玉盈,透過兩位法律專業人士各自在司法實務中的寶貴經驗出發,探討台灣司法體系的現況、備受關注的國民法官制度,以及法律扶助在社會安全網中不可或缺的關鍵角色。

周漢威考取律師資格時,正值法律扶助基金會成立之際。他回憶當時的情景:「法扶其實是民國93年的1月7號通過法律扶助法,民國93年的7月1號成立的,所以我們那一群剛好民國92年考上律師、在受訓的過程中,成立法扶的前輩們就來宣傳法扶。」這個時代背景讓他和部分同期律師們在職業生涯初期就投入法律扶助工作,他強調,過去台灣並沒有一個正式的制度來處理公益案件,大多是律師事務所自行承擔。然而,當國家設立法律扶助基金會,並由國家提供資源,號召律師以市價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的酬金接案時,這「某種程度上也宣示了國家對於弱勢者跟需要幫助者的支持」。
《我們與惡的距離Ⅱ》的角色與情節,讓周漢威看到了加害人與被害人之間複雜的心路歷程。例如,醫師馬亦森作為被害人,經歷傷痛甚至精神問題,需要協助;而加害人胡冠駿,其案件則牽涉到曾輔助他的少年保護官;劇組細膩地描繪了加害人與被害人內心轉化的過程。這部劇不僅反映了當下社會狀況,也令社會反思:「我們怎麼協助加害人?我們要怎麼樣協助被害人?我們應該要給予什麼樣的資源?乃至於這些資源夠不夠的議題的探討」。

法律扶助可維護當事人權益,更有助釐清真相
劇中反映精神疾病患者強制住院的法律程序,周漢威說明,台灣在民國101年到111年期間,立法院對此議題曾有深刻討論,主要因為台灣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並修正《精神衛生法》。
「目前嚴重病人要住院,還是要經過醫師診斷,他是嚴重病人,也就是說他有與現實脫離的一些奇思幻想,那至於他在具體行為裡面,發生自傷傷人之虞,也就是他有傷害別人,或者是傷害自己的情形,經精神醫師診斷,有住院的必要的時候,才會發動強制住院。」
更重要的是,周漢威強調精神衛生法修法後的核心理念:「他(立法)最重要的目的是支持病人在社區平等生活這件事情,換言之,住院只是一個手段,我們只是透過住院的方式,給他妥適的治療,這個病患終究還是要回到社區,跟大家一起生活;他是我們社會共同體的一部分,他並不是一個孤立的個人。」
周漢威特別解釋《精神衛生法》第62條(已通過但尚未施行)的重要規定:當嚴重病人被警方緊急安置在精神鑑定處所時,該精神醫療院所應通報中央主管機關提供必要之法律扶助。他認為,這能在第一時間確保病患的人身安全和法律權益,更重要的是幫助「釐清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以及「國家的制度到底出了什麼問題?」這也呼應了司法體系日益意識到,在人身權益保障的重要事項上,法律專業介入協助,不僅是維護當事人權益,更是幫助釐清真相,推動社會進步的關鍵。

少年犯罪防護的法律角度:輔佐而非對抗
透過劇中少年犯罪問題的觀察,周漢威詳細說明了台灣的少年司法制度。「12歲以上到未滿18歲犯案的這些少年,國家是有一個特殊的刑事程序去做處理的,當少年犯案的時候,首先就像劇裡面的少年調查官一樣,他會去做仔細的調查,然後提出一個調查報告給法官。」
在少年案件中,律師的角色特別不同:「律師在少年案件裡面,它其實不叫做辯護人,他其實叫做輔佐人;它其實是幫少年瞭解現在司法的程序是什麼。」周漢威分享實務經驗:「我們自己專職律師在做少年案件的時候,我們就會問他們說你為什麼不想去上課啊?發生了什麼事情?那你應該要去上課啊,如果你不想去上課,你有沒有其他地方可以去?」
這種做法的目的是「讓法院知道少年當事人跟現有的環境或是現有的人際關係,已經產生一定的變化跟隔絕,還不到國家需要用法院的強制力,乃至於甚至刑罰去處理你這個事件的必要。」

需要在3至5天內審案,我們準備好了嗎?
《與惡Ⅱ》也呈現台灣目前國民法官制度的施行現況。民國112年開始實施的國民法官制度是台灣司法改革的重要里程碑。周漢威解釋制度設計:「是三個法官加上六名抽選出來的國民法官組成一個合議庭,來決定案件要怎麼審理。」這個制度的目標包括提升司法透明度、增加人民對法律的了解,以及落實司法決定由專業人士與民眾共同參與。
然而,制度實施過程中也面臨挑戰。周漢威提到,在一般案件中,法官是「全知的神」,能看到全部卷證與事實;但在國民法官案件中,卻只能拿到簡單的起訴書,並要在「3天或5天內」完成密集審理,時間和精力都極為有限。他坦言:「在這件事情上,我不覺得我們的司法與法官準備好了。」
台灣國民法官參與量刑,卻缺乏具體的「量刑指引」
周漢威同時強調,在國民法官制度下,辯方面臨著嚴重的「資源不對等」和「沒有武器、沒有調查權」的困境。他解釋,檢察官在偵查中就擁有完整的調查權,雖法律規定要同時注意對被告有利與不利的事項,但實際上基於「隧道效應」(註)和起訴的必要性,檢察官往往著重於調查對被告不利的事證。當這些不利證據收集完畢後,進入審判當辯方向法院聲請調查對被告有利的證據,法院在判斷必要性時,因為無法看到全卷資料,可能導致心中產生疑義而「限縮辯方的空間」。
法扶專職律師唐玉盈則以親身經歷補充了辯護方的實際困難。她表示,在訪談證人(如被告的同事、朋友、甚至家人)時,常會「碰壁」,許多人一聽到要訪談就掛斷電話。即便解釋是法律扶助,對方也多半拒絕。
周漢威則補充,在社會輿論強烈要求對被告施以「最嚴格的最嚴厲的刑罰,乃至於超過法律刑度的刑罰」時,這些知情卻非被告親近者「怎麼敢說出他們已知的事實?」,這種社會氛圍導致「真實的資料不能被呈現到法院上面」,使得國民法官無法像《與惡Ⅱ》的觀眾一樣,清楚了解被告(如劇中的胡冠駿)的成長背景和行為動機,而只能看到他造成的可惡結果。這使得「判決或決定所依據的資料是有欠缺的」,對整個制度不利。
周漢威引用劇中律師「王赦」的台詞:「人生有多難,量刑就有多難」,強調量刑的複雜性和技術性。
周漢威指出,國民法官制度在量刑方面存在巨大不確定性。他提到,國外(特別是英、美法系)經過「幾百年、幾千年的嘗試」,有些國家決定不將量刑交給陪審團,因為量刑是「非常個人的,是非常具體的,也是非常技術性的」。
然而,台灣讓國民法官參與量刑,目前卻缺乏具體的「量刑指引」。這導致判決的「歧異性」高,對於司法的安定性、被告和司法人員的「可預期性」都構成巨大挑戰。
他舉例說明,過去肇事致死若有賠償和解,第一次犯罪者常有機會獲得緩刑,但現在,即使賠償並得到被害人諒解,被告仍可能入獄,且刑度不低。
「假如我們今天把這麼重要的責任託付給國民法官跟法官一起來做決定,那我們要給國民法官怎麼樣的知識基礎,讓他去做出合乎一般司法可預見的一個相當的判決,理由是什麼?」這個問題反映了制度運作中的核心困境。
「修復式司法」旨在建議原告與被告的對話
劇中馬醫師與胡冠駿的對話場景,體現了修復式司法的精神。周漢威認為,被害人家屬常常會問「他為什麼這樣?為什麼是我?那我該怎麼辦?」,這些問題在傳統司法程序中往往無法得到充分回應。
他提到,「修復式司法是在偵查或是審理的過程中,讓檢察官跟法官在原告、被告雙方都願意對話的狀況之下,能夠有一個好的空間,在專業的人士的協助下,開始進行這樣子的一個對話。」
他特別強調,即使在重大案件中,「大部分的被告,就像我剛剛講的精神衛生法的病患一樣,最終我們還是希望他回到這個社會的,最後他還是我們社會的一份子。」這種觀點體現了修復式司法的根本理念:不是簡單的懲罰,而是修復關係、重建社會連結。
理解犯罪背後的成因,才能預防悲劇重演
對於法扶制度存在的意義,周漢威認為這代表台灣法律社會的珍貴價值:「不論你是誰,不論你犯了什麼錯,在中華民國的法院體系裡面,還是會找到一群有經驗的人,他願意站在你的身邊幫你說話。」
周漢威以劇中羅譽為例,說明問題的複雜性:「羅譽就是他爸爸入獄了,媽媽有點狀況,最後也因意外住院了,又沒有社會資源,所以他最後面就變成詐欺的車手。」

唐玉盈則從更深層的角度思考犯罪成因。受到台大法律學院名譽教授李茂生和律師顧立雄影響,她認為:「我們今天不會犯罪,不見得是我們比較善良,而是我們沒有面對那個人那樣的困境。」她強調,理解犯罪背後的原因,才能真正預防類似悲劇重演。
律師唐玉盈引用曾經指導過他的律師顧立雄所提「走在冰上」為比喻:有的人運氣好,走在結實的冰上,沒有意外;有的人則走在薄碎的冰上,掉下去了。若此時沒有人伸出援手,甚至需要「多一點的人去拉住他」,他可能就會不斷下墜。唐玉盈在法扶工作中也發現,當事人多多少少都處於「智能表現落在邊緣」,可能沒有到智能不足,但「學校成績不好,或是天生比較脆弱,又或者是小時候有一些創傷」。
周漢威進一步分析法扶對案件的分析數據:「在詐欺犯裡面,法扶協助的被告,我們看到絕大多數是身心障礙者、是原住民、是少年。」這個數據揭示了犯罪背後的社會結構問題。
《與惡Ⅱ》中揭示「這個犯罪當事人他今天會落到這個地步,那中間到底是哪裡出了錯?」。唐玉盈也認為,在犯罪被告身上,可能不是一個階段出錯,而是「好多個階段都出了錯,然後才會越錯越大」。因此,解決之道是「希望了解並想辦法去改善我們的環境」,才能「減少這些事情的發生」,而不是僅僅「把這個人殺掉之後,我們好像那個恐懼感就安全了」,因為這樣「根本的原因還是沒有找到」。她以鄭捷案為例,認為其快速執行,導致社會無法深入了解其家庭背景與犯罪根源。

法扶為什麼要幫「壞人」?
周漢威進一步指出,社會大眾常會對法律扶助的刑事案件,尤其是重案,產生質疑,認為「我們為什麼要幫壞人?」。然而,周漢威進一步解釋:「司法資源的挹注,如果單看表面的數據,你就會覺得法扶一半案件花在刑事案件裡面,又以重案為居多,我們為什麼要幫壞人?可是你仔細數據分析下去,或是看了《與惡Ⅱ》的時候,你就可以知道那個壞人並不是像大家想像的那些人,並不是開名車、住豪宅這樣的,可能是像羅譽這樣子,家裡面錢都付不出來的小朋友、是經濟弱勢者。」
他認為,法扶的工作是在案件和司法程序的「後端」進行協助和釐清,而這本身就是「一個國家、政府應該要去處理面對的問題」。周漢威強調法律扶助制度的社會功能:「這是一個社會的煞車,這是一個社會反省的機會。」
周漢威指出,如果沒有透過專業的法律程序讓社會理性思考犯罪成因,「最快的方法就是解決提出問題的人,於是我們就處理那一個人,但是解決提出問題的人,這件事情問題並沒有被解決,也不會被解決。」
而他也對那些即使酬金微薄、社會壓力巨大卻仍願意投入工作的法扶律師們表示欽佩。
為當事人發聲,還須承受龐大社會壓力
法扶基金會執行長周漢威也強調,以目前認真經手國民法官案件的律師「很困難」找,部分案件「需要三個,甚至往往三個律師還不夠」。唐玉盈也認為,辯護過程倘若能有更多的協助的律師以資討論、互相交換意見,並共同承擔和分擔策略,以充分應對來自法官和檢察官的壓力。
周漢威分享擔任相關案件辯護人的心路歷程,以及面對社會質疑時的堅持與省思,認為辯護重案,特別是死刑案件的律師心理壓力極大,常常會「午夜夢迴會被驚醒」,質疑自己在檢辯審理過程是否「當時如果再勇敢一點,會不會改變什麼?」
而在死刑案件辯護過程,建立當事人信任關係也是一大挑戰。周漢威指出:「當事人某種程度上會自我放棄的比例相當高,他們的律師並不是他家人幫他請的,是從零信任關係裡面開始的。」往往法扶律師們甚至會自掏腰包帶會客菜,用最基本的關懷來打開當事人的心房。
談及社會異樣眼光,周漢威坦承過去在林于如案件中曾遭受質疑電話,甚至需要法院安排特殊通道避開媒體。然而,他對當時的選擇感到遺憾:「我人生一個最懊悔的事情,如果讓我再一次以我現在的狀況,我會出去跟媒體記者好好的說明。」他認為,身為律師應該勇敢面對質疑,為當事人的權益發聲。
唐玉盈同時提到法庭上的兩難處境:「我們有時候會很猶豫,我要不要對抗法官,當法官他很強勢,可是你會很猶豫--萬一我得罪了他,會不會反而對我的當事人很不好?」
這種在專業責任與現實考量間的掙扎,突顯了法扶律師工作的複雜性。
法律扶助制度是社會正義的最後防線
正如周漢威所說:「我們真的社會大眾必須要給被告,乃至於辯方,乃至於整個司法制度一個適度的空間,讓他們好好地、專業地、嚴謹地完成他們應該要做的工作。」
而法律扶助制度不僅是提供法律服務,更是社會正義的最後防線。
在面對複雜的社會問題時,我們需要的不是簡單的懲罰,而是深入的理解、專業的協助,以及持續的制度改革。只有這樣,台灣才有機會真正建構一個更公平、更人道的司法制度,讓每個人都能在法律面前得到應有的保障和尊重。
註:「隧道效應」(Tunnel effect)指人處於急迫或壓力情境下,很可能只在意短期、淺薄的訊息,難有中長期的考量,就像進入隧道只看得見眼前的景物,難以用寬廣視野面對大環境。
【延伸推薦】
影集|《我們與惡的距離Ⅱ》:故事從一場超市縱火案展開,24歲的嫌犯造成五死十二傷的慘劇,這案件成為施⾏國民法官制度後,首個可能判處死刑的案例。大火也燒出了六個家庭交織的命運,時有錯過又彼此牽扯,他們背負著各自生命故事跨越了20年,復仇、背叛、傷害、墜落,並相互救贖,在隨機殺人事故之後,命運會將這六個家庭帶往何處?
文章|「國民法官」與職業法官有相同審判權力,審判量刑需看見被告的人生困境
作者:《我們與惡的距離Ⅱ》議題短片小組
責任編輯:陳珊珊
核稿編輯:李羏
出刊日期:202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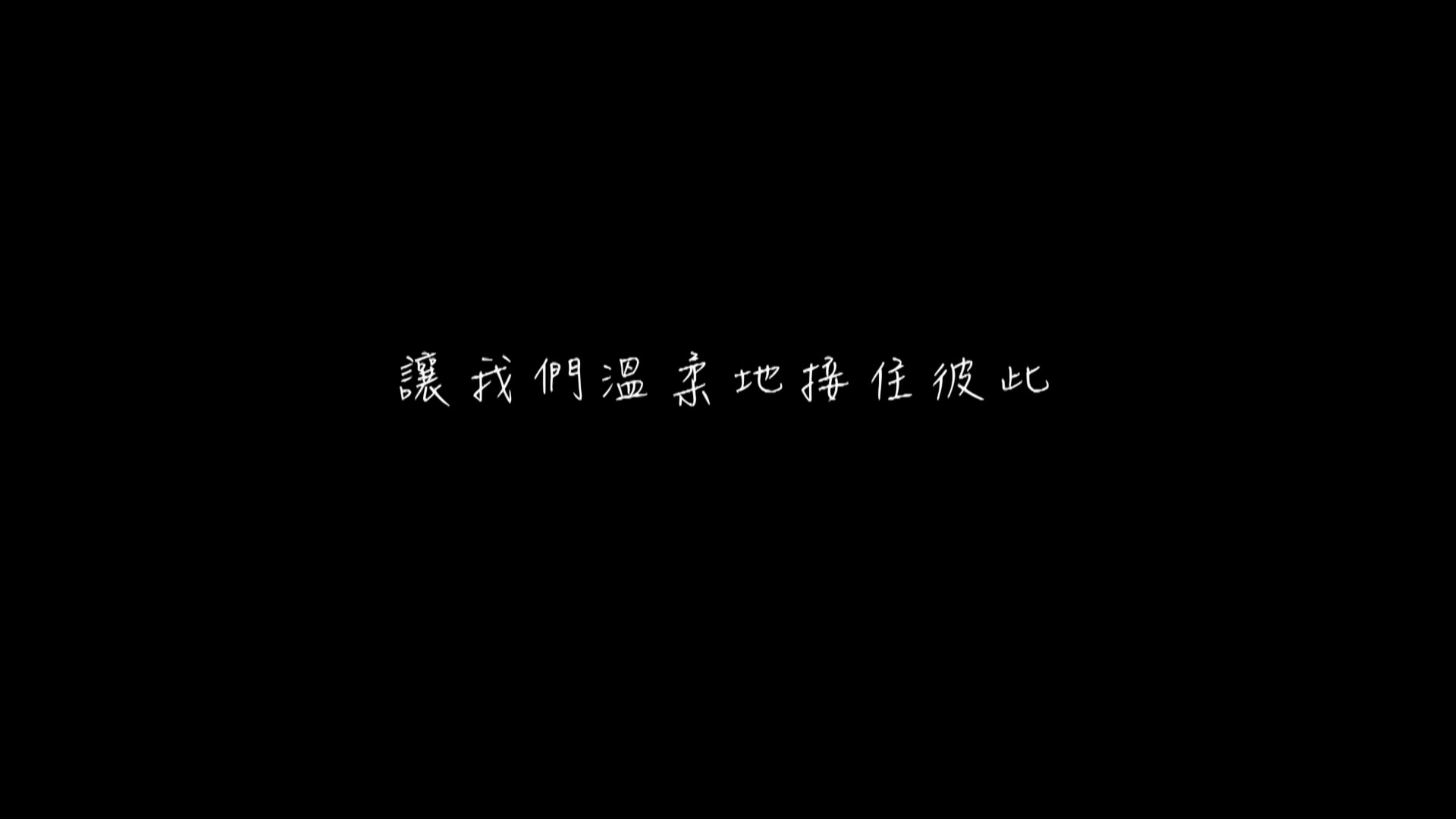
讓我們溫柔地接住彼此
